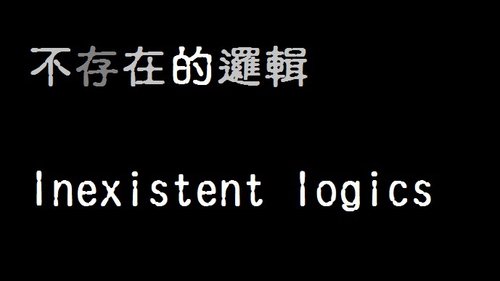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向
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
甚崇﹐家徒甚慇。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
不群﹐深為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
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
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為
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余抵長安﹐居于布
政裡。嘗游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
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妖
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
鞭于地﹐候其從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
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長安之熟者以訊之。
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
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
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
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
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
當整妝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
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
乎﹖” 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
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
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
艷冶。生遂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
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
近。生之曰﹕“在延平門外數裡。”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
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雲夕。道
裡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
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
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
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
許。俄徙坐西堂﹐帷幕帘榻﹐煥然奪目﹔妝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
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
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
食﹐未嘗或舍。” 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
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
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
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蓆﹗”生遂下階﹐拜而
謝之曰﹕“願以己為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
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
儕類﹐狎戲游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余﹐資財仆馬蕩
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
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荐酹求之﹐可乎﹖”生不
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
宿而返。策驢而後﹐至裡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
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見一車
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
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
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
髮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
亭﹐竹樹蔥茜﹐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
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
曰﹕ “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
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
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
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
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
往﹐至舊宅﹐門扁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
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
矣。”征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
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
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
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
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 訪其誰氏之
第﹐曰﹕“此崔高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雲遲中表之遠至者﹐未
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
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余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
于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
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
﹐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
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佣凶器
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
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
聲﹐而相贊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佣
之器于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
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
聚至數萬。於是裡胥告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
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輿威儀之具﹐西肆皆不
勝﹐師有慚色。乃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
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
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
頃﹐東肆長于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
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
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為眾所
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
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
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婿
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
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
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于同黨曰﹕“向
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
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眾中。豎
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
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
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
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昵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嘆。令二人葦
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
勺飲﹐經宿乃活。月余﹐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
同輩患之﹐一夕棄于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
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持一破甌巡于
閭裡﹐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糞壤窟室﹐晝則週游廛肆。一
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淒
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裡垣﹐北轉第七
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飢凍
之甚。”音響淒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
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
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
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
我之罪也。”絕而復甦。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
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卻睇曰﹕“不然﹐
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
設詭計﹐舍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
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
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
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為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
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
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
可奪﹐因許之。給姥之余﹐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
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余﹐方荐水陸
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
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
昔之藝業﹐可溫習乎﹖” 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游﹐
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
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
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
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
以俟百戰。”更一年﹐曰﹕ “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
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
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
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
多士﹐爭霸群英。” 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征
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
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
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
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死。”
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
令我回。”生許諾。月余﹐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
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
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
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
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
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劍門﹐筑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
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
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
靈芝產于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
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
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
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
能逾也。焉得不為之嘆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
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
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
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雲。
|
| 研國夫人李娃,原是長安的妓女。節操和品行高貴奇特,有很值得稱道的地方,所以監察御史白行衛替她作了節,介紹她的事跡。天寶年間,有位常州刺史叫榮陽公,這裡略去他的名字,不作記載。當時名望很高,家中人口很多。他五十歲那年,有一個兒子剛滿二十歲,長得聰穎俊秀,且有文才,傑出不凡,深為同輩人所佩服。榮陽公更是喜愛並器重他,說:「這是我家的千里馬。」
公子受郡縣推薦進京參加秀才科考試,臨走時,榮陽公為他在服裝、珍寶、車馬等方面做了充分的準備,計算好進京後的日常生活費用,並對他說:「我看妳的才華,應當一考就奪魁。現在我為你準備了兩年的費用,並且給得更多一些。是為了幫助你實現你的願望。」公子也很自負,把考取功名看得像在手心裡寫字那麼容易。
他從毗陵出發,經過一個多月到達長安,住在布政里。有一次他逛東市回來,從平康里的東門進去,要到西南方拜訪朋友。當他到了嗚珂巷時,看見一所住宅,門庭不很寬廣,但房子卻很整齊幽深。門半開著,有個年輕姑娘靠著一個梳雙髮的婢女站在那裡,美貌嫵媚,世上從未見過。公子突然見到她,不由自主地停下馬來看了半天,徘徊不忍離去。於是假裝把馬鞭掉在地上,等待僕人前來,吩咐他拾起。其間公子不斷偷看這姑狼,姑娘也轉過眼睛斜盯著看他,顯出很愛慕的神情。但他最後還是不敢說上一句話,就離開了。
公子從此心裡像若有所失似的,於是暗中訪得朋友中熟悉長安的人,向他打聽那位姑娘。朋友說:「這是妓女李氏的家。」又問道:「她可以求得嗎?」回答說:「李家很富有。從前和她往來的多是貴戚豪族,她得到的賞錢很豐厚。不花上一百萬,不能打動她的心。」公子說:「衹怕事不成,即使用掉百萬,又有什度可惜呢?」一天,公子穿戴整齊,帶了許多隨從前去。公子敲她家的門,一會兒有個侍女開了門。
他說:「這是誰的府上?」侍女不回答,跑進去大聲叫道:「前些時掉馬鞭的公子來啦!」李娃大喜道:「你暫且叫他等一下,我要打扮好了再去見他。」公子聽到後心中暗喜。侍女便把公子引到影壁邊,看見一個頭髮花白的駝背老太婆,她就是李娃的母親。公子上前下拜並恭敬地說:「聽說這裡有空屋,願意出租給人住,真是這樣嗎?」老太婆說:「衹怕它簡陋狹窄,不能讓您滿意。怎麼敢談出租呢?」說完就邀請公子到客廳裡去,客廳很華麗。她和公子面對面地坐下,便說:「我有一個小女兒,略知歌舞技藝,喜歡見客人,我打算讓她來見見您。」於是她就叫李娃出來。衹見李娃眼睛明亮、手腕雪白,走起路來美極了。公子驚訝得趕忙起身,不敢抬頭看她。他和李娃拜見後,寒暄了幾句,李娃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艷美動人,公子從未見過。待重新就坐,李娃為公子沏茶斟酒,所用的器皿都很潔淨。他們在一起過了很久,太陽已落山了,鼓聲響了四下。
老太婆問他住得遠不遠。公子騙她說:「在延平門外,有幾里路。」他希望因路遠而被留下。老太卻說:「更鼓已敲過了,您應當趕快回去,不要違犯禁令。公子說:「我有幸得到妳們的熱情接待,並和妳們親近談笑,不覺時間已到晚上,歸路遙遠,城裡又沒有親戚,我怎麼辦呢?」李娃說:「您不嫌這裡冷僻簡陋的話,既然正打算租來住,先歇一宿有什麼關係呢!」公子多次用眼睛去看老太。老太婆說:「好吧!好吧!」公子便叫僮僕拿出兩匹細絹,讓她們用它來準備一頓晚飯。
李娃笑著制止說:「賓主間的禮節,不應該這樣。今晚的費用,願由我們窮苦人家出,請你一起吃些粗荼淡飯,其他的就等以後再說吧。」她堅泱推辭,始終不答應收下細絹。不一會兒他們移坐到西邊廳堂,堂內殿帳床榻,光彩奪目;妝奩枕被,也都奢華漂亮,於是點上蠟燭,端上菜肴,山珍海味十分豐盛,吃完飯後,老太起身走了。公子和李娃談話這才親熱隨便起來,逗趣調笑,盡情極歡。公子說:「前些時候我偶然走過妳家門,正好遇見你在門邊。打那以後心裡常思念妳,即使睡覺吃飯從未有片刻忘記過。」李娃回答說:「我心裡也一樣。
公子說:「今天到這裡來,不單是租房子,而是希望實現平生的願望,但不知道我的運氣如何呢?」話未說完,老太太來了,問他們在談什麼,公子就統統告訢了她。老太太笑著說:「男女之間,愛戀的欲望原本是存在著的。感情如果契合,雖是父母之命,也不能制止,我這小女實在醃陋,怎麼夠得侍候在您身邊呢?」公子立即走下臺階,拜謝她說:「我甘願獻身做奴僕來報答您。」老太於是認他作女婿,他們又暢飲了一番才散。等到天亮,公子把他的行李全部搬來,就住在李家了。從此他匿跡藏身,不再和親友通消息,每天和倡伎優伶一流人物聚會,吃喝玩樂。袋裡的錢用完了,他便賣掉馬匹車輛,後來又賣了家僮。過了一年多,錢財僕人馬匹全部沒有了。慢慢地老太太對他越來越泠淡,李娃對他的感情卻越來越濃厚。
有一天,李娃對公子說:「我和你相愛已一年,還沒有懷孕。常聽說那竹林神廟,很靈驗,我打算去進獻祭品向神靈祈求,可以嗎?」公子不知道這是她們的計謀,竟然非常高興。他便把衣服押在當鋪裡,準備了牛羊豬三牲和祭酒,和李娃一起去竹林祠懤告,他們在那裡住了兩宿才回去。公子騎驢跟在李娃的車子後面,到了宣陽里北門,李娃對他說:「從這裡向東轉到一個小巷裡,是我姨媽家,我們去歇一下,並看看她,可以嗎?」公子照她的話做了。他們向前走不到百步的路,果然看見一個可通車馬的大門。往裡張望,見宅內很寬敞。李娃的婢女從車後叫住公子說:「到了。」公子就下了驢,剛好有一個人出來,問道:「誰呀?」回答說:「是李娃。」那人就進去稟告。一會兒,有一個老婦人從裡面出來,年紀約四十多歲,一見公子就問道:「我外甥女來了嗎?」李娃走下車來,老婦人迎上來說:「為什度長期沒有來呢?」說完她倆相視而笑。李娃介紹公子拜見了她。
見過之後,就一起走進西戟門的偏院裡。院中有山亭,竹樹青 翠,地塘水榭幽雅罕見。公子對李娃說:「這是姨媽的私人住宅嗎?」李娃含笑不答,用其他的話支吾過去了。一會兒獻上茶點水果,很珍貴稀有。剛過一頓飯的光景,有個人騎著快馬,滿身大汗飛馳而至,對李娃說:妳媽媽得了急病,病很重,幾乎都不認識人了。妳最好馬上回去。」李娃對姨媽說:「我心裡亂極了。我騎馬先回去,然後讓馬車回來,你就和郎君一起來。」公子打算跟她去。她姨媽和婢女說了幾句話後,就揮手叫公子等在門外,說:「老太婆快要死了,妳應該和我商量一下辦理喪事,以解決李娃的燃眉之急,怎麼能就跟著回去呢?」公子衹得留下,一起計算喪禮和齋戒祭祀的費用。天色晚了,馬車仍沒送來,姨媽說:「到現在還沒有回信,怎麼回事呢?你趕快去看看她們,我接著就趕來。」公子就走了。到了李氏老宅,見門窗緊緊地鎖著,還用泥封起來了。
公子大驚,問她的鄰居.鄰居說:「李家本來就是租這裡的房子的,租期已滿了。房東收回了房子。老太太已搬家,而且已有兩天了。」公子問:「搬到哪裡去了?」答道:「不清楚是哪個地方。」公子打算趕回宣陽里,去問她的姨媽,但時間己經太晚了,估計路程怕已趕不到了。他衹好脫下衣服,換頓飯吃,租了床住了一夜。公子憤怒到極點,從夜晚到天亮,一直沒合過眼。天剛亮,他便騎著驢子上路了。到了李娃姨媽的門口,連連敲門,有一頓飯的工夫也沒有人應聲。公子大喊了好幾聲,有一個做官模樣的人慢慢出來,公子急忙問他:「姨媽在嗎?」答道:「這裡沒有什度姨媽。」公子說:「昨天傍晚在這裡,為什度把她藏起來了!」又問這是誰家的房子,那人答道:「這是崔尚書的住宅。昨天有個人租了這個庭院,說是等候她遠道而來的表親。還沒有到晚上就走了。」公子驚恐迷惑,氣得像要發狂,但又不知該怎度辦,衹得回去尋找布政里的舊宅。
住宅主人憐憫他,拿來飯菜給他吃。公子又怨又很,三天不曾進食,結果得了很重的病,十多天後病情更加嚴重了。住宅主人怕他一病不起,就把他搬到了辦喪事的店鋪裡去。他奄奄一息地過了一天又一天,整個鋪子的人都同情可憐他,他們輪流餵他吃東西。後來公子病情略微好轉了一些,靠著拐杖能站起來了。從此喪事店鋪每天讓他幹些事,管管靈賬,得些報酬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幾個月後,他漸漸地康復了。每當聽到唱挽歌,就自嘆不如死去的人,嗚咽流淚,控制不住自己的悲傷。回去後就學唱挽歌。公子本是個聰敏的人,不多久,挽歌就唱得特別好了。即使整個長安城也無人可與他相比。起初,這裡的兩家辦喪事的店鋪,互相爭奪高低。東面店鋪裡的車轎都特則華麗,沒有能比得上的,衹有挽歌唱得差。東面店鋪主人知道公子挽歌唱得精妙絕倫,就湊集了兩萬錢來雇用了他。同夥中的老前輩又把自己最拿手的本領傳授給他,並秘密地教公子新的唱法,還給他幫腔。
連著幾十天,沒有人知道這件事。這兩家店鋪的主人相約說:「我們各自在承承天門街展示出辦喪事的用具,比試高低。輸者罰錢五萬,用來備酒食請客,好嗎?」雙方都答應了。於是約人立下文契,簽名劃押作保證,然後展出用具。男女老少都來參觀,聚了好幾萬人。於是地保報告捕賊官,捕賊官報告京兆尹。四面八方的人都到了這裡,整個城裡街巷裡空無一人。兩家喪鋪從早晨開始展出,直到中午,依次擺出車、轎、儀仗之類的器物,西面店鋪都不能取勝。主人覺得面子過不去,便在場子南角搭了個高臺。有個長鬍子的人,抱著個大鈴走來,簇擁在他身邊的有好幾人。於是他鬍鬚一抖眉毛一揚,握住手腕,點著頭,登上高臺,這才唱起了(白馬)這首挽歌。他依仗它一向取勝,環顧左右,旁若無人。博得了大家齊聲贊揚,自認為獨一無二,沒有對手能壓倒他。
過了一會,東面喪鋪主人在場子北角上也設了個臺子,有個戴黑頭巾的少年,身邊跟著五六個人,手拿長柄羽毛扇走上臺來,這就是公子。他整整衣服,動作慢悠悠的,清了一下喉嚨便開始發聲,一副悲不自勝的樣子。他唱的就是(薤露)的挽歌,發聲清朗,聲音振顫著林木。挽歌還沒唱完,聽歌的人己經哀嘆悲傷掩面哭泣了。西面店鋪的主人被眾人譏笑,越發慚愧難當。他偷偷地把輸的錢留在前面,便溜走了。四週觀眾驚訝地瞪著眼睛望著公子,他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在這之前,天子剛下詔書,命令外地的長官每年來京城一次,稱之為「入計」。
當時碰巧公子的父親在京城,他和同僚們換了便裝俏俏前去觀看。有個老僕,就是公子奶娘的丈夫,看到公子的舉止言談,想去認他卻又不敢,也就傷心地流下淚來。公子的父親感到驚奇而問他。老僕便稟告說:「唱歌人的相貌,酷似老爺的亡子。」榮陽公說:「我兒子因為多帶了錢財詖強盜謀害,怎麼會到這裡呢?)說完,也哭了。等他們回去後,僕人找了個機會又趕回那裡,向同夥打聽道:「剛才唱歌的是誰?唱得這樣的好!」都說:「某某人的兒子。」探問他的名字,公子之名已經改過了。
僕人極度震駑;慢慢過去,走近了仔細看他。公子看見僕人就變了臉色,就轉身打算藏進人群中去。僕人便抓住他的衣袖說:「您不是公子嗎?」說完就兩人抱頭痛哭。老僕便用車把他載了回去。到了住處,父親責備他道:「品行墮落到了這般地步,污辱了我的家門!你還有什麼臉來見我?」於是父子二人步行出去,到了曲江西杏園東,父親剝去他的衣服,用馬鞭抽打了他幾百下,公子受不了這個痛苦,昏死了。父親扔下他獨自走了。
當公子被什麼人帶走時,公子的師傅便讓和他關係好的人暗中跟著,這時,他回來把公子的遭遇告訢了同夥,大家都為此而傷心。師傅讓兩個人拿蘆蓆去埋葬他的屍體。他們趕到那裡時,初覺得公子心口仍有點熱氣。)一人忙把他扶起來,過了很久,公子才稍微緩過氣來。他們便一同抬著他回去。用蘆葦管子灌湯水餵他愒,過了一夜才蘇醒。一個多月後,他的手腳仍舉不起來。那些被鞭打的地方都潰爛了,髒得很,同伴們都開始討厭他了,一天晚上,他們把他丟在了路邊。過路人都可憐他,常常丟些吃剩的食物給他,他才得以充饑。一百天後,公子方能拄著拐杖站起來。他穿著布棉襖,棉襖上有上百個補丁,破爛得像掛著的鵪鶉。手裡拿著一個破罐,來來去去在里巷間,靠討飯過日子。
從秋天到冬天,夜晚鑽進廁所、地窖中,白天就在市場、店鋪裡周遊。有一天下了大雪,公子被寒泠和饑餓逼迫,冒雪出去,乞討的聲音非常淒慘,凡聽到的人無不淒傖痛心的。當時雪下得正大,人家的大門大都不開。公子到了安邑里東門,沿著里牆向北走,過了七八家,有一戶大門恰好開著左半邊,這就是李娃的住宅。公子不知道,便連聲疾呼:「餓煞啦!凍煞啦!」聲音淒切,令人不忍心聽。
李娃在房中聽到,對婢女說:「這一定是公子。我聽出他的聲音了。說完趕快跑了出來。衹見公子骨瘦如柴,滿身疥瘡,已經不像人樣了。李娃心裡很激動,就對他說:「您難道不是鄭郎嗎?」公子氣憤得昏了過去,口裡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衹是點點頭罷了。李娃上前抱住他的頸脖,用繡花短襖裹,扶著他回到西廂房,失聲慟哭道:「使你今天落到這個地步,是我的罪過啊!」她哭昏過去,良久方又醒過來。老太婆大驚,奔跑過來,說:「怎麼啦!」李娃說:「這是公子。」
老太婆忙說:「應當趕走他。怎麼讓他到這裡來!」李娃嚴肅地回頭瞟了她一眼說:「不該這樣。他是好人家的子弟。想當匆他駕著華麗的大車,帶著裝滿財寶的行李,來到我的屋裡,不到一年錢就花光了。我們合起來設下詭計,拋棄並趕走了他,簡直不像是人做的事。讓他喪失志向,被親戚朋友看不起。父子之道,是天性,使他父親恩情斷絕,打死他後又拋棄了他。公子如今淪落到這個地步,世上的人都知道是為了我。公子的親戚滿朝廷都是,有朝一日當權的親戚查清原由,災禍就會降到我們頭上了。何況欺天負人,鬼神也不保祐,不要自找禍殃吧。我做您女兒,至今有十年了。算起你為我花的錢來,已不止千金。現在您六十多了,我願用您後一十年吃穿的費用來贖身,我要和他另找住處。那住的地方不會遠,早晚能夠來問安侍候您,您如答應,我的心願也就滿足了。」
老太婆料想她的志向已經不可改變,衹得答應了。李娃給了老太婆贖金之後,還剩下百金。她就在北邊角隔四、五家處租了一個空院子。她於是替公子洗了澡,做了衣服。做了湯粥,潤通他的腸道;再用酥奶潤潤他的內臟。十多天後,才開始給公子吃些山珍海味。頭巾鞋襪,都取貴重的給他穿戴,沒過幾個月,公子肌膚豐滿了些,過了一年,康復得像當年一樣了。又過了些時候,李娃對公子說:「你的身體已經康復了,志氣已經旺盛了。你應該深思靜慮,默想從前的學業,可以重新復習嗎?」公子想了想,說:(衹記得十分之一了。」李娃叫駕車出門,公子騎馬跟在後面。到旗亭南偏門賣書的店鋪書,她讓公子選擇好一些書買下,算起來共用了百金,然後他們把書全都裝上車運了回來。李娃叫公子拋棄雜念一心學習,不分黑夜白天,孜孜不倦。李娃經常賠伴公子坐在一旁,直到深夜才睡。
每看到他疲倦了,就勸他練習詩文來調劑。過了兩年,學業大有成就,天下的典籍,沒有一種沒讀過。公子對李娃說:(可以報名應考了。」李娃說:「不行。還應讓學業更加精通熟悉,以應付各種考試。」又過了一年,李娃說:「可以應考了。」公子就一舉考上了甲科。名聲傳遍了禮部。即使是老前輩看到他的文章,也無不肅然起敬,都想把女兒嫁給他但又不能如願以償。李娃說:「你現在還不行。現在的秀才,假如得了一次科名,就自以為可以得到朝廷的要職,美名揚天下。你以前行為不端、品德又卑下,不同於其他文人。應當磨煉鋒利的武器,以此求得再戰再勝,才能結交眾多文人,在名士中稱雄。」公子從此越發勤奮刻苦,聲望越來越高。那一年,正趕上科舉考試的大比之年,詔令四方的才子應考,公子報考直言極諫科,名列第一,授予成部府參軍的職位。三公以下的官員,都做了他的朋友。公子將要去上任,李娃對他說:「如今恢復了你本來的面目,我不再有負你了。我願以我的餘年,回去贍養老媽媽。你應當和高門大族的小姐結婚,讓她主持家政。
在你們的姻族中或姻族外結親,都不要糟塌自己。努力自珍自愛。我從此就離開了。」公子哭道:「你如果拋下我,我就自刎而死。」李娃堅決推辭不從,公子苦苦請求,而且越來越懇切。李娃說:「我送你渡過江,到達劍門後,就讓我回來。」公予衹好答應。經過一個多月的路程,到了劍門。他們還沒來得及接著走便接到了授薪官職的詔書,是公子的父親從常州奉詔入朝,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
過了十二天,榮陽公到達。公子就遞上名帖,在傳遞文書的驛站中拜見了父親。父親不敢認他,但看到名帖上祖父三代的官職名諱,才大吃一驚,讓他登上臺階,撫摸著他的後背痛哭了好久,才說:「我們父子和好如初吧。」於是問他事情的原由,公子詳細述敘了事情的始末。榮陽公非常驚奇,問李娃在哪裡。公子回答說:「她送我到了這裡,我正打算讓她回去。」
父親說:「不能這樣。」第一天,他讓車馬和公子先去成都,讓李娃在劍門,單租一幢房子讓她住下。第二天,讓媒人來說了媒,六道大禮全部備齊,然後來迎接她,於是他們成了正式的夫妻。李娃嫁過來之後,一年到頭主持祭祀都很合乎規矩,她遵守婦道,治家嚴格有條理,很受公婆喜愛。往後又過了幾年,公子的父母都亡故了,她依禮守孝很盡心。竟然有靈芝生長在她守孝的草廬邊,一個花穗開了三朵花。當地長官把這事上奏給了皇帝。又有幾十隻白燕子,在她的屋脊上築了巢。皇帝感到驚奇,更加提高了賞賜的等級。守孝期滿,公子連連陞遷重要的職務。
十年當中,做過好幾個郡的長官。李娃也被封為洴國夫人。他們生了四個兒子,都做了大官,最低的尚且做到太原尹。弟兄的婚娶都是門第最高的人家,京城內外的望族,沒有誰能比得上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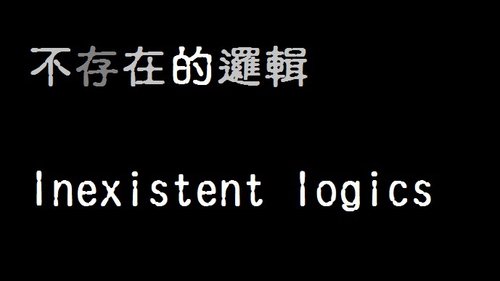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